
纪录片导演周轶君成为母亲之后,开始不自觉地为孩子的教育而焦虑,于是,她前往世界各地探访当地的家庭和学校,了解不同的教育形态,希望给自己一个答案。以下是周轶君在“一席”演讲上讲述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心得感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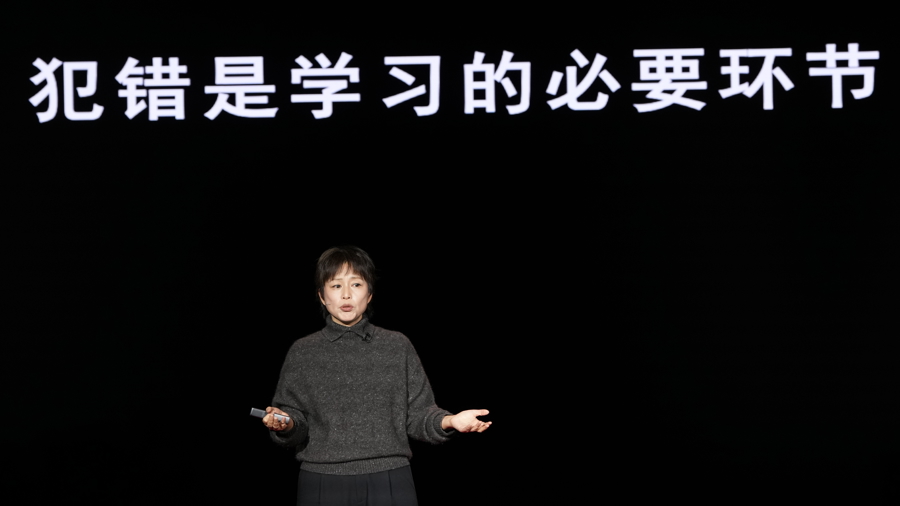 周轶君在演讲中。(图片由“一席”演讲提供)
周轶君在演讲中。(图片由“一席”演讲提供)
我有两个孩子,2018年的时候,他们一个6岁,一个3岁。关于他们的教育,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:上代人的教育方式已经不合时宜,但是轮到我自己教育孩子,却似乎也找不到新的方式。
于是,作为一个多年的国际新闻记者,我决定按照我最擅长的方式,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去寻找答案,看看这世界上有没有更好的教育方式,看看它们是什么样子的。从2018年到2024年,我和我的团队去了10个国家进行拍摄,第一季去了芬兰、日本、英国、印度和以色列,第二季又去了新加坡、法国、德国、新西兰和泰国。
选择这些国家是有原因的。比如,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很小,却是全世界人口比例中拥有大学学历最多、初创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,我很好奇他们的创造力从哪里来。又比如,一些中国父母放弃很多带着孩子到泰国留学,我很好奇他们会经历什么。
 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海报。
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海报。
『关注把人培养成人的教育』
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剧烈变化的世界,科技发展、地缘政治、意识形态都在发生着迅猛的变化,而有句话叫“百年树人”,教育的影响注定是非常缓慢的。
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拍摄和追寻的,正是关于如何把人培养成人的教育。我们希望通过观察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童年教育,不仅能学习如何把更好的教育教给下一代,也能理解成年人是如何被自己的童年所塑造、从而成为今天的样子的。
我们的第一站是芬兰。芬兰给我的震撼非常大,这里的中小学竟然没有考试、没有排名,也不鼓励任何形式的竞争,甚至在课堂上也没有标准化的答案。
在一堂森林课上,老师让学生闻各种植物的味道、观察各种树木的样子。我以为老师期待着孩子说出植物正确的名字,但不是,老师让学生用自己的想象力给这些植物命名。比如,一棵树可以叫作“雨的味道”,因为那天刚下过雨。对于小学生来说,只要在课堂上发挥想象力就好。等他们到了中学,再开始学习系统的知识。
而在地球的另一端,新加坡的孩子们正在刷题和考试。
有个小男孩才5岁,他的妈妈就让他提前学习小学一年级的内容。他的补习老师告诉我,在新加坡,很多孩子从5岁到考大学之前每天都需要补课,没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。这些补习机构通常在大商场里,是一些没有窗户的小隔间。有些孩子在学校上完半天课来不及回家,就直接来到这里吃午饭、做作业。
有一个孩子给我展示他的书包有多重,大人开玩笑说里面装的是金条——其实装的是沉甸甸的复习资料和书本。
『千差万别的教育样貌』
行走在不同的国家,我看见了各种不同的教育样貌。
印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。全球500强公司的CEO中,有30%为印度裔,他们特别善于协调不同族群的关系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。在印度的课堂上,学生告诉我,一堂没有学生挑战老师的课是不完整的。学生们敢于在没有想好一个完整的答案时就举手发言,他们做事情也是这样,先开始,边干边学。
而在日本,孩子们从小学习如何通过团结协作成就一个强大的集体。每个人被要求注意自己的仪表和姿态,要照顾他人的情绪和需求,克制个人的情感。所以在日本,当众哭泣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。
法国的哲学课则让我大开眼界。在课堂上,不超过10岁、最小只有五六岁的孩子们讨论着什么是幸福、什么是爱。老师问孩子们:如果你爱的人去世了,那么爱仍然存在吗?有一个孩子回答:爱是你自己的决定。
这个男孩在课后跟我说,他仍然不敢付出爱,因为他经历过好朋友的背叛,他的好朋友跟别人讲他的坏话。让我惊讶的是,这些孩子在这个年纪就能如此顺畅地讨论自己的负面情绪,而我作为成年人,却很少有机会好好思考这些问题。
在德国,小学生的必修课不是哲学,而是一些生活技能,比如德国所有的小学生都必须通过自行车驾照考试。作为一个来自“自行车王国”的成年人,我也参加了考试,结果累积了8个错误点,没有通过。因为他们的交规太严格了,从戴头盔、打手势到转弯幅度和速度都有严格的要求。
在英国,我去了所谓的贵族学校。我发现这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,把漂亮的制服、烦琐的礼仪作为重要标志。相反,这里最重视的是如何服务社会。拥有男爵头衔的卢卡斯先生告诉我,今天英国社会对贵族的定义只有一个词:service(服务)。贵族精神,就是服务社会的责任和担当。
而在以色列,十几岁的女孩们已经开始创业,她们非常自信地在名片上印上CEO、创始人等头衔。以色列的孩子们认为,这个年纪应该开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,而不是留在教室里抄板书。
旅程中,我的观念一次次被刷新。我在成长过程中,不断被教育应该避免犯错和失败,我们认为这两个词语是非常负面的。在课堂上,如果老师提问,学生们通常会把头低下来,因为觉得说错、出丑是羞耻的。但是在以色列和德国,人们告诉我,失败和犯错是教育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。在希伯来语中,“失败”不是结局,而是意味着你可以重新开始。在德国,我问过一位职业学校的校长关于德国制造的秘密。他告诉我,德国制造以高质量著称,而高质量背后的秘密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问题。一个德国妈妈说:犯错是学习的必要环节。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犯错,说明他都没有尝试,又怎么能真正学到东西呢?
教育的多样面貌、多元观点让我眼花缭乱,仅仅是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理念,就让我的视野变得开阔,把我从狭隘的焦虑中拉了出来。因为,教育的可能性,就是生活的可能性。
 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剧照。
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剧照。
『巨大的差异就在细节中』
作为导演,我更希望观众能够在片中看到教育的细节,因为教育理念可能都差不多,但巨大的差异就在细节中。
当我们谈论保护孩子的时候,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好的?
在柏林一个住宅区的儿童乐园,我发现这里的游乐设施非常坚固。用于固定的铁链特别粗,铆钉特别大,还有专人定期检查。这样一来,孩子们玩耍时,家长不需要一直盯着。
还有一个场景让我非常震惊。在柏林的一间教室里,讲授性教育课程的老师正在展示一些教学工具。看到这些模型时,我非常脸红。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教育过于透明,但正因如此,在欧盟国家中,德国的青少年早孕率是最低的。
有一次,我亲身体验了芬兰的课堂。那堂课的内容是让学生和老年人互相画对方的肖像,观察时间在人脸上留下了什么痕迹,从而理解时间的概念。老师鼓励我也加入课堂中,我谦虚地表示我不太会画画。老师觉得我的说法很奇怪,她说:这些画不是拿来比较的,有人说过你的画不好吗?在上课的过程中,我看到孩子们并不在意谁画得好、谁画得不好,他们都沉浸在画画本身。他们觉得每个人画得不一样,是因为每个人观察到的、看到的东西不一样。
我突然意识到,“比较”“竞争”这类的观念已经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,我觉得自己“画得不好”,其实是把自己置于一个评价体系中。但是在芬兰,竞争是不必要的。学习是为了生活,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评价。
在日本,我同样看到孩子们为了生活而学习。日本的中小学校园里没有专职保洁员,所以包括清洁厕所在内的工作都需要孩子们自己完成。每个小学生入学的第一天,妈妈都会为他们准备一块抹布,用来打扫卫生。
而我在新西兰一所学校的所见所闻,让我重新思考“自由”这个概念。刚一进学校,我就看到孩子们像从树上长出来一样,他们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方,可以捡起树枝互相追打,他们荡秋千的高度让人心惊胆战,骑着滑板车冲下坡道的速度像飞一样。这是课间休息的一幕,操场上没有一个老师监督他们。新西兰的校长告诉我,让孩子们自己往高处攀爬,其实是把对危险的控制权交给了孩子。他们需要学会保护自己,明白什么是安全,什么是自由的边界。
没有竞争、没有排名的芬兰,却曾经取得过全世界第一的教育成绩。没有普遍的乐器考级制度的德国,大部分德国人都会演奏乐器。这让我想起罗素说过的一句话:儿童最大的欲望,是长大成人的愿望。孩子们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,快快长大,但很多时候,这种成长却被大人的不放心阻挡了。
『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』
每一次这样的看见、听见,对我和观众而言都是思维边界的突破。看到了这么多的不同、这么多的细节,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: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教育方式?究竟有没有最好的教育?
要回答这个问题,让我用新加坡来举个例子。
在新加坡,有一个全民皆知的漫画形象,叫“怕输先生”。“怕输”就是怕落在别人后面,为此需要不停地竞争,哪怕竞争是不必要的。在我们的语境中,这可能叫“想赢”,只有超过别人才能安心。
“怕输”已经渗透到了新加坡人的骨子里,在教育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新加坡的中小学校园里悬挂了很多标语,当时我看了心里一惊。那些标语上这样写着——“新加坡是我们的家,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”“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”“我们自己保卫自己的国家”“我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,我来这里是要成为优秀的人”。
这些话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含义。新加坡建国的过程并不容易,他们曾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威胁。今天,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,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,自己是一个被海水围绕的岛国,缺乏自然资源,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。这些新加坡的小学生每天上学时都要提醒自己:为了国家的生存,需要我努力学习。这是动力,也是巨大的压力。从这些标语中,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教育会面临如此严酷的竞争。
走过那么多国家,我越来越意识到,教育其实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,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。并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,只有适合自己土壤的教育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他人的智慧和经验,来改良自己的教育土壤。
『改变教育从具体的细节入手』
教育的改变,同样要从具体的细节入手。
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播出后,我与几位中国乡村的校长、教师做了一档播客节目,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。
一位叫陈秋菊的老师在四川山区里教了十几年书,她发现现在农村的孩子居然不认识农作物。于是,她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带到了田野里上课。当时正是豌豆花盛开的季节,孩子们在大自然中学习语文,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连接。
何欢老师是湖北一所乡村中学的校长。他刚刚接手这所学校时,学校的氛围非常低落,教职员工纷纷离职,学生没有心思上学。何欢曾在英国考察,他发现英国学校的学生可以自己组织俱乐部,发展各种兴趣爱好。他意识到,只有让学生喜欢上学校,才能让他们喜欢上学习。于是,学校组织了足球、篮球等体育活动,还举办运动会,开展推铁环、抖空竹等传统竞技项目,给300多名学生都发了奖状。结果,这所学校的氛围完全改变了,不少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。何老师说:我最初做这些事,并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改变,但我非常确定,让孩子们通过兴趣找到人生的方向,这远比上大学更重要。
这两位老师的行动,让我想起了在印度看到的一些教育工作者,他们同样通过自己的努力,改变着教育的细节。
印度的“玩具大王”库布塔先生,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。他看到印度的贫困人口众多,很多穷孩子连玩具都没有,于是自己设计了100多种使用废旧物资制作玩具的方法,并建了一个网站,无偿地和所有人分享。
我曾经到过印度的一个偏远乡村。这个村子偏远到什么程度?从新德里出发,我坐了3个小时的车、半个小时的船和一个多小时的三轮车才到。那里的孩子当然没有机会接触电脑和互联网,但志愿者们却在这里架起了互联网,办起了“云中学校”。每天下午,他们会邀请全世界的志愿者,通过屏幕给孩子们讲述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。
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们也许无法改变印度贫困群体的现状,但他们可以通过改变教育的细节,来改变孩子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未来。
『观察他者的意义何在』
走过这么多国家、看到这么多千差万别的教育方式后,我发现,不同的教育方式其实是为了适应不同国家、文化以及人群的特定需求而形成的。
正如孩子们也是各不相同、多种多样的,我们有时会期待每个孩子都成为栋梁,但他们就像植物一样,各有不同。有的很快就能开花结果;有的怎么施肥、浇水都不开花,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;有的可能看起来并不漂亮,但生命力特别顽强、特别茂盛。
改良土壤的确是改变教育的重要一步。如果没有人们内心的改变、认知的改变,教育改变终归还是无法完成的。
纪录片播出后,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多次收到观众的反馈。有一线教师和师范学校的老师告诉我,他们把《他乡的童年》中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带到了自己的课堂;有家长说,他们更有信心教育自己的孩子了;有单身的年轻人说,他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、重新养育自己。
我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?就是为了在教育的细节中看到他者的存在、他者的智慧,听听、看看其他“园丁”是怎么做的,再思考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教育。
当然,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:看了那么多好的教育方式,对你自己的家庭教育有什么影响?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,孩子们有自己的特点和轨道,他们不会完全按照家长的期待或要求成长。之前说到,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,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。这里我要再加上:家庭教育其实就是父母的“三观”,而社会教育则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影响。
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孩子,而是成年人的认知和内心。我常说互联网配资网站,纪录片其实是一场行动。纪录片拍出来只是行动的一半,另一半需要大家看完纪录片之后,改变认知和观念,并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。这才是我们观察他者的意义所在。
联华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